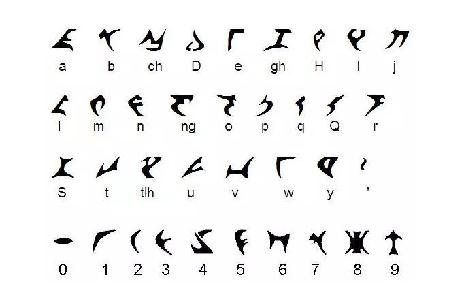
克林贡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语言创作迎来了又一个高潮。一位叫马克·欧克朗 (Marc Okrand)的语言学家为《星际旅行3:石破天惊》(Star Trek III)创作了克林贡语(Kingon)。 前几部《星际迷航》中出现的克林贡词汇屈指可数。欧克朗以这些词语为根据,建立了一套基础的发音规则和语法。在此之后,他就只创造剧本需要的词汇了。这门语言本质上是个幻觉,像是情景喜剧的客厅里摆着的舒适的家具一样。 “近看很真实,但远看却会发现,那只是一堆木板支撑起来的夹板罢了。”在电影工作人员的劝说下,他赋予了这门语言血肉。他在电影上映后出版的克林贡语词典卖出了超过30万本。

《权利的游戏》里创造的多斯拉克语
如果说欧克朗是像建立数集一样创造克林贡语,那么彼得森就是像建筑师一样创造虚构语言。他创造《权力的游戏》里游牧战士部落讲的多斯拉克语(Dothraki)时,设计好了每个单词的历史渊源。他还假设这门语言古时候就存在,所以顺带发明了这门语言的古用法,其中包括了剧中并不需要用到的上千个词汇。欧克朗告诉我,彼得森不仅仅是“建了一栋楼,他还做了考古学研究,考察楼房下的这片土地上方曾经有过些什么。” 1999年,彼得森18岁,他在二手书拍卖会上发现了蒙塔古·C·巴特勒(Montagu C. Butler)编写的《世界语教程》(Step by Step in Esperanto)后,第一次对发明语言产生了兴趣。一年后,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语言学入门课上,学到了形态学的知识。他借鉴了一条定律:语言规则就像工具一样,他可以用来创造属于他的语言,创造出他喜欢的用法。 他创作的第一门语言是从阿拉伯语和世界语中获得灵感的,但在他尝试翻译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时,他意识到了这门语言 “是个彻底的败笔”。他告诉我:“我只是在用一种很糟糕的办法重新创造出英语而已。”如果英语中某个物体有对应的用词,那么彼得森的语言里也同样有之。这个语言和英语极为相似,因此水手、海员、水手长都和英语有对应的词语。 毕业后,彼得森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语言学硕士学位,继续在语言领域深造。他虽然总共学了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但自谦能流利使用的也只有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 之后,他在奥兰治县的社区大学教了两年英语,很不满意这份工作。后来正在创作的讽刺小说也停笔了,也并未发表。在这段时间里,他对语言创作的兴趣却从未减少。借托尔金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活在身体里的爱好”。他的梦想就是以此谋生。 2009年,他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权利的游戏》创作人联系了他合作建立的美国语言创作协会,通过多斯拉克语创作竞赛来招募工作人员。 虽然当时在电视节目里,语言创作还没掀起热潮,但制作人们似乎很清楚地意识到,胡言乱语一通,观众并不会买账。 毕竟,这部电视剧是根据一个畅销书系列改编的,读者们正正是被书中的复杂构思和精巧细节而吸引的。此外,电视观众的性质已经变了。 有了电视录像机和社交媒体,粉丝们越来越热衷于抽丝剥茧:他们将演员的服装分类好放上众包式百科,把角色的扭曲表情做成动图,为了争论剧中的矛盾和时代错误而在推特打起了口水仗。高昂的制作费用和昂贵的制作效果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值。如果剧中的语言是应付性地乱说一通,那么就会流失一部分观众,但并不会失去全部观众。 彼得森上交的多斯拉克语文件长达180页,打败了几十个对手。到了2013年,《权力的游戏》已经是电视上最多观众观看的剧情类节目了。其他主流电视网络也嚷嚷着要在剧里加入发明语言了。 彼得森接到了许多工作,成为了全职的语言创作人。虽然一门发明语言能够生存发展下去是件极其罕见的事,但他却被成堆的观众翻译要求淹没了。他尽力回复所有请求,有必要时还会即兴创作出来。 不久之前,一位《权力的游戏》的粉丝给他提了一个特别的要求:能用多斯拉克语说出“社会学女生”吗?她想把这个词纹在身上。使用多斯拉克语的那个世界里,马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喷火龙盘旋在天空中。也许没有必要说,这是一个没有社会学的世界。 彼得森告诉她:“多斯拉克语里没有这样一个词,也永远不会有这样一个词。”尽管如此,他还是提供了一句翻译:nayat fin avitihera vojis sekke,意思是盯着别人看很久的女生。
学习编造的语言并不容易,彼得森想要让演员们能够学会它。他曾试过在电话里和演员们排练台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教,得教上好几个小时。有时要花上好几天才能读对发音。 《抗争之城》(Defiance)里,妮可·加利西亚(Nichole Galicia)饰演的是一个说Kinuk'aaz的外星人。她和我说,有一次,她在开拍前几个小时新加了台词。她根本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全部学会。拍到一半时,她脑袋突然一片空白,想到什么Kinuk'aaz语的词汇都说了出来。 “我的台词本来是‘我看到你就恶心,你丢了我们族人的脸’,结果我说成了‘节日快乐’。”当时片场上的人都不知道说错了,导演还觉得那一幕是她演得最好的一场戏。可是加利西亚觉得很羞耻,她哭着跑到演员休息车上,打电话给彼得森道歉说,她屠杀了他的语言。 他安慰道:“你肯定是想太多了,拍摄的时候或许并没有那么糟。如果说得很不好的话,还可以配音。”最后那幕戏用了配音。

高等瓦雷利亚语
彼得森上完《今日秀》的第二天早上,我在他的酒店里上了一堂语言课。我幻想着自己是《今日秀》的主持人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擅长高等瓦雷利亚语。 我以为彼得森能够教我怎么用高等瓦雷利亚语点咖啡(“只加奶油,不加糖”)。但原来和社会学一样,咖啡也不属于《权力的游戏》里面的世界,因此高等瓦雷利亚语中不具备点咖啡所需的词汇。

Castithan语
彼得森说,我可以退而求其次,学《抗争之城》里一个外星种族的语言Castithan语。这个种族和人类有交易来往,因此有接触过这种饮品。他查阅了iPad里317页的字典,找到了咖啡(kofya)、奶油(krima)和糖(shugara)这几个词。 他在纸上随手写下了翻译,给我常速读了一遍:“Kofya ksa zhulawa, krima ksa fivi, shugara kanwa.” 到我读了。虽然发音听起来很简单,但我开口时还是说的很慢:“Kof-ya ksa jah-lah-wah—”。彼得森打断了我说:“这是个u。” “读来听听,Zhu-lah-wah。”重复和纠正了几分钟后,我读这句话时舌头还是打结了。 彼得森评价我说:“发音不错,音调不行。” 他也说, Castithan语“很饶口”。《抗争之城》的演员们也很头疼。我听到这话后就振奋了起来。同样让我振奋的,是在课程开始,他正在思考教我哪种语言时,我听到他自言自语喃喃地说出的那句话:“我可以用《抗争之城》里的一种语言来说这句话,不过我说得不是很好。”
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
译者:周静
编辑:刘秀红
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文谈”公众号:cdwent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