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法国哲学家萨特在《恶心》(Nausea,1938)里写道:“一个人永远是故事的讲述者,他生活在自己和周围其他人的故事里。他透过这些故事看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他努力像叙述故事一样过日子。”生活不会停下来,但照片可以让瞬间停留。不过,萨特肯定曾坐在巴黎花神咖啡馆里,扪心自问:真的要告诉别人我在喝这杯咖啡吗?真的要把所做的每件事都一一述说,而且做每件事的目的都只为述说吗?“你得做出选择,”他总结道,“享受生活,还是讲述生活。”要么享受喝咖啡的时光,要么花时间拍照上传Instagram。

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对叙事型的生活有着同样的担忧。虽说麦金太尔认为,现实生活是对想象生活的一种模仿,威廉姆斯却认为,区别“文学虚构人物”和我们这些“真实人物”的关键在于,虚构人物的一切从最开始就是完整的,而我们却不是。换句话说,虚构人物不需要自己决定未来。威廉姆斯因此认为,麦金太尔忽略了一点——我们虽然可以用叙事的眼光理解不断逝去的生活,但我们同时必须思考未来。当面临抉择时,我们不可能停下来思考何种选择最符合故事的叙述连贯。
的确是这样:有时我们确实会参照自身的生活方式来作出决定,但在此之前,我们必定会先权衡一些更加本质的问题,而不是先考虑我们的公众形象。威廉姆斯认为,事实上,如果通过参照自己的“人物形象”来生活,那么我们就容易陷入一种不真实的困境,一种有悖于原始面貌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你一板一眼地做起平时自然而然就做出的事情,却发现刻意起来反而更难。如果你一边走路一边思考该如何走路,没准最后会突然摔一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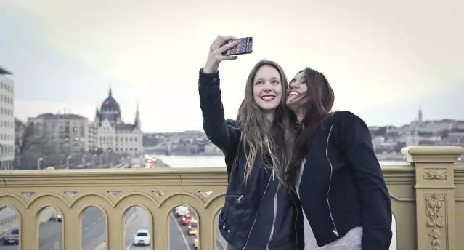
十几年前,当威廉姆斯写下这些时,自拍还不甚流行。如果威廉姆斯的观点是正确的,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如今渴望对自身有更多的了解呢?从某些方面讲确实如此,只有读懂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正如当代哲学家大卫·威尔曼所说,人类为了理解自己的生活,构建了某种公共形象,这种形象不是为了纯叙述而存在,而是一种可供解读的图像,让我们得以通过某种媒介阐释自己。即使是流落荒岛、与世隔绝的鲁滨逊,也需要塑造某种表现自己的载体,有了这种载体,他才能记录下每天的生活轨迹。
正是这种对于解读的诉求,产生了私密与公开之间的界限划分:为了让自己能够被理解,我们必须构建一种自我表达,而为了构建这种自我表达,我们必须在“呈现什么”和“保留什么”之间做出取舍。因此,我们选择隐藏自己的私密空间,并不是因为感到羞耻,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其无益于自我表达。而在这里,摩根的自拍照,只是自我表达这一人类基本诉求的写照。

威尔曼可能会说,自拍的流行,是脸书、推特等自我表达工具迅速增多的结果。这些新形式的出现压缩了私人空间。我们都渴望掌控自己的呈现方式——如果说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渴望,那么社交媒体的出现无疑极大满足了这一点。当时的威尔曼认为我们应该稍加克制,但那还是14年前。如果是在今天,我猜他可能会声讨那些眼花缭乱的自我表达标签(比如#这样醒来,#此刻的心情,#生活,#我)。不过没关系——毕竟他自己也说过,每个人都有权利展示或者隐藏自己认为合适的东西。
不管你是否把人生当成一种叙事,生活都离不开关于“呈现什么”和“保留什么”的选择,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取舍。而“公开”和“私密”的定义,既然对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群体来说各不相同,那么它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也就不甚相同。所以,每当看到室友自拍时,我依然会觉得尴尬,就像不小心撞见他们换内衣一样。
原文选自:万古杂志(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译者:梁笑
编辑:钦君
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文谈”公众号:cdwent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