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
很烦——我们来拍摄患者的时候,总被告知患者情况太糟糕不能见我们。他们当然糟糕,不然怎会住院。
2014年6月-7月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都在申请进入重症病房拍摄,但医院不同意。他们对患者有监护职责,禁止我们拍摄没有民事能力的患者,而且我们也无法向他们保证会隐瞒患者身份。如果不提及身份,又怎么能在纪录片里完整地表现布罗德莫的生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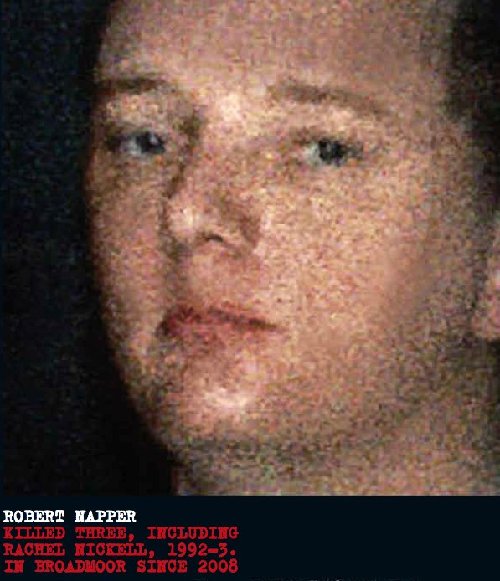
2014年7月11日
最后,我们获准了进入克兰菲尔德(Cranfield)重症监护病房,但院方要求镜头只能对着工作人员拍摄。这个病房不同寻常,只有九名患者住在这里。他们是这所医院里最严重的患者,但不意味着他们实施过最恶劣的罪行。我们看到这里的病人精神很不稳定,空气中弥漫着威胁的味道。他们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空旷的走廊回荡着他们的喊声和哭叫。有人一直在大笑,还有人在撞门。房间很大,每个房间都有独立卫生间。这些人出房间的时间很短,而且要有多达六名工作人员看护,看起来就像“押送”——一左右各有一名护士抓着胳膊,一名护士在前面倒着走,随时警告可能发生的威胁,还有几名护士跟在他们前后。判断患者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工作人员怎么给他们送饭——有些人的饭通过小窗口送进去,还有人则可以短暂开门送饭。
一名患者从病房进入了一个有小门的封闭院子,呆了五分钟。他和我说话,通过铁栅栏和一名工作人员下棋。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持续不了几分钟。过了一会儿,当工作人员告诉他回房间的时候,他激烈反抗起来。于是不得不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八名工作人员才将他安全送回。这里的工作人员平均每周要被患者袭击五次。
2014年8月-10月
我和编辑吉米·海伊(Jimmy Hay)一起制片,商量怎么处理医院要求的限制条件。布罗德莫的很多员工每天都和这个国家最失常的人打交道,我收集的材料就是对他们献身精神的最好证明。很多人以为进了布罗德莫就再也出不来了,但的确有患者最终能够康复,离开那里前往监控等级较低的环境,甚至还有一些人能重返社会。
我大体的感觉是:从孩童时代,社会就有职责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得到适度地关怀和保护,让他们免受身体虐待、性虐待和心理虐待,这样他们才能完整地成长起来,减少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倾向。
我做制片已经三十多年了,经历过极度恶劣的环境。但综合各种情况来看,布罗德莫精神病院的这次拍摄是迄今为止最困难的一次。
原文选自: radiotimes
(编译:smartypants,编辑: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