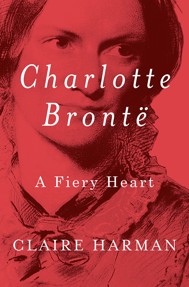勃朗特三姐妹将社会施加给她们的重重限制化成了铸就伟大作品的原料。
在勃朗特姐妹之前,还没有一本著作能像《圣经》(Bible)那样衍生出其他众多著作。但是,勃朗特姐妹几乎做到了这一点。露卡丝塔·米勒(Lucasta Miller)在2001年发表的讲述“勃朗特热”(Brontëmania)历史故事的《勃朗特的传说》(The Brontë Myth)一书中这样写道:“自从1857年,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发表了举世瞩目的《夏洛蒂·勃朗特的生平》(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以来,几乎每年都会出版关于勃朗特姐妹的各种类型的传记性文字——从报纸文章到长篇报道,从茶巾到戏剧、电影、小说。”今年是夏洛蒂·勃朗特诞辰200周年,整个勃朗特文化产业都在庆祝,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也因此忙碌了起来。美国出版的全新夏洛蒂·勃朗特传记,作者是著名作家克莱尔·哈曼(Claire Harman);以勃朗特为主题的文学侦探小说;取材于《简爱》(Jane Eyre)的连环女杀手故事;受著名的“读者,我嫁给了他”(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简爱》最后一章的第一句话)启发而作的短篇小说集;还有以《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女管家丁耐莉(Nelly Dean)为主角的同人小说“自传”。去年的亮点是描写艾米丽青少年时期的青年小说,还有一部名叫《勃朗特家的储物柜:九件物品里的三段人生》(The Brontë Cabinet: Three Lives in Nine Objects)的深度散文集:借用夏洛蒂、艾米丽以及安妮的物品,作为了解19世纪和找寻她们各自特质的突破点。更不用说与她们相关的专题论著了。
我没有理由不怀疑,“勃朗特热”是一种宗教崇拜。如果他们不是迷恋拜物文本,劲头十足地进行润色编织,怎能称得上“圣书之民”(Peoples of the Book)的美誉?犹太人用“米德拉什”(midrash,希伯来语“解释”“阐述”之意)一词指代宛如明线一般穿梭于《摩西五经》(Torah,《圣经》的首五卷)中的狂热幻想。该词代表了为原文中断节或矛盾的地方编织古怪神奇的前史或神话故事的过程。不过《米德拉什》可不仅是犹太法学博士的圣经注释。你可以把福音书(Gospels)叫做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的米德拉什,《圣人们的生活》(the lives of the saints)是《基督故事》(Christ story)的米德拉什,《古兰经》(Koran)则是上述全部经典的米德拉什。
一些勃朗特迷——也就是读者,我也是其中之一—乐于成为勃朗特热的教徒,钻研大量勃朗特作品的米德拉什,从中探寻那些让人敬畏、充满神秘感的蛛丝马迹。那位贫穷又不擅社交的名叫夏洛蒂的前家庭女教师,和她更糟糕的妹妹艾米丽,守着牧师父亲在约克郡荒野上的房子,远离伦敦文化圈,怎能创作出几乎比任何一本19世纪英国小说和诗歌都生动形象的作品来呢?弗吉尼亚·伍尔夫(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在1925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简·爱》和《呼啸山庄》的文章里,这样描写这一奇迹:
“又一次翻开《简·爱》,我们无法压抑那种怀疑,我们将会发现,她想象中的世界和那荒野的教区牧师住宅一样,是古老的、维多利亚中期的、不合时尚的,那种地方只有好奇者才会涉足,只有虔诚者才会保存。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情翻开了《简·爱》,仅仅读了两页,所有的疑虑就从我们的头脑里一扫而光。”
如果说夏洛蒂的小说是一阵狂风的话,那么艾米丽的《呼啸山庄》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暴风雨。伍尔夫说道,艾米丽笔下的人物,甚至连鬼魂都有“一股如此强烈的生命气息,让它们超越了现实”。(正如其他读者一样,伍尔夫忽略了三姐妹中年纪最小的妹妹安妮,一位称不上小说家或诗人的作家;还有她们的兄弟布兰威尔(Branwell),他在成为诗人和艺术家的道路上穷途末路,最后染上酒瘾。)伍尔夫后来创作出了另一更为有名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如果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风俗道德禁锢了夏洛蒂的才能,她可能也会创作出这样的作品。